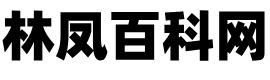三年前我在深圳华强北的某个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,偶遇一位做存储器批发的潮汕老板。他指着柜台上密密麻麻的芯片苦笑:“这些玩意儿比白粉还贵,但利润都让老外赚走了。咱们啊,就是给美国人打工的搬运工。”他掐灭烟头时的那声叹息,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。
如今再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(简称“大基金”)这盘棋,突然觉得像极了那个下午的隐喻——我们确实受够了当搬运工。
但问题在于,砸钱真的能砸出芯片自主吗?
大基金二期募资超过2000亿的新闻出来时,我在某个行业社群里看到段子手调侃:“这数字听着吓人,但台积电一年的资本开支都不止这个数。”笑完又觉得心酸。我们总习惯用宏大数字安慰自己,却忽略了芯片行业最残酷的规则:钱只是入场券,而且可能是最不值钱的那张券。

我采访过某家拿到大基金投资的传感器企业CEO,他在酒过三巡后吐真言:“政府资本像婆婆,给钱时痛快,后续天天问你什么时候生孙子。”他说的“生孙子”指的是短期变现能力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玩过的击鼓传花——资本把芯片项目炒成击鼓传花的游戏,最后接盘的往往是真心想做技术的那帮傻子。
最讽刺的是,某些被投企业高管私下抱怨:“拿政府的钱比拿市场的钱更累。要应付的报表比研发文档还厚,会议纪要写得比电路设计还精细。”某次我亲眼见到一位院士在评审会上拍桌子:“你们到底是选科学家还是选会计师?”

但话说回来,若没有这场豪赌,我们连牌桌都上不去。
去年参观某国产EDA软件公司时,CTO给我看了组触目惊心的数据:全球EDA市场三大巨头垄断超80%份额,而国内所有厂商加起来市场份额不到5%。“没有大基金前期输血,我们连和Synopsys打价格战的资格都没有。”他办公室挂着的书法写着“愚公移山”,落款竟是大基金某位高管。
这种悲壮感让我想起早年间看过的西部片——明知赢面不大,但必须有人先拔出左轮手枪。只不过芯片战争的子弹是钱,而装弹时间需要十年起步。
最近某半导体论坛上,有个90后工程师的话特别戳心:“我们现在做的可能不是最先进的芯片,但就像修青藏铁路——不能因为现在高铁快就不修普通铁路了。”台下掌声雷动时,我注意到前排几位白发专家在偷偷抹眼角。
或许大基金最珍贵的不是催生出多少个上市企业,而是给这个焦虑的时代保留了最后一点理想主义火种。就像我认识的那位放弃硅谷百万年薪回国的设计大牛说的:“总得有人去做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,虽然这话现在听着像傻子宣言。”
站在2023年的十字路口,看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,突然觉得大基金像极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——在炮火中守护火种,在绝望中保持体面。至于最终能培育出多少个“杨振宁”,或许要留给二十年后的后人评说。
此刻窗外又传来中芯国际扩建新生产线的消息,恍惚间想起华强北那个潮汕老板最近发的朋友圈——他转型做国产芯片分销了,配文是:“这次不搬货,改种树了。”
树能不能成活还不知道,但至少,我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撒种了。
原创文章,作者:林凤百科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mftsp.com/4852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