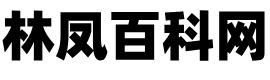去年夏天,我在上海陆家嘴的一家咖啡馆里偶遇了一位老友——姑且叫他老陈吧。他当时正盯着手机屏幕,眉头拧成了死结。“又跌停了,”他啐了一口,“这帮做空的孙子,真会挑时候。” 我看着他杯子里晃荡的美式咖啡,突然觉得那颜色像极了被稀释的恐慌。
老陈是个典型的多头信仰者,坚信“长期持有”才是王道。而我呢?大概从五年前亲眼目睹某新能源巨头被做空机构撕掉画皮、股价腰斩的那一刻起,我就对“做空”这回事产生了某种病态的好奇。不是幸灾乐祸,更像是一种逼近真相的冲动——当所有人都在欢呼时,总得有人冷静地问一句:“万一这盛宴是纸糊的呢?”
—
一、做空不是恶魔,而是市场的“清道夫”

很多人一听“做空”就咬牙切齿,觉得这是趁火打劫的秃鹫行为。但说实话,如果没有做空机制,股市可能会变成一场更肮脏的骗局乐园。还记得瑞幸咖啡吗?当年那份89页的做空报告像一记闷棍,打醒了多少沉浸在“国货之光”美梦里的人?有时候我在想,做空者其实是市场里的“病理医生”——他们专挑光鲜表皮下的腐烂部位下刀,虽然过程血腥,但结果可能是救了一群盲目输血的人。
当然,这种“正义感”很容易变味。我见过一些对冲基金打着“揭露真相”的旗号,实则联合媒体散布恐慌,甚至恶意捏造数据。这就像让警察兼职当小偷——监管的缺位让做空成了一场无差别屠杀。去年我尝试小仓位做空某家消费股,仅仅因为怀疑其现金流造假,结果却被突如其来的政策利好打爆仓位。那一刻我意识到:做空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活,它更是一场人性与规则的缠斗。
—
二、散户做空?更像是裸奔进雷区
总有人问我:“普通人也该学做空对冲风险吧?” 我的回答通常是:“如果你还在问这个问题,最好别碰。” 这听起来很傲慢,但背后是血淋淋的教训。
做空天然违背股市的数学规律——股价上涨空间理论是无限的,但下跌最多跌到零。这意味着你的亏损可能无限大,而盈利却有天花板。更残酷的是, timing(时机)的重要性被放大到变态级别。去年新能源板块回调时,我认识的一个程序员用期权做空龙头股,明明判断对了趋势,却因为爆仓线设置太高,倒在黎明前最后一小时。他苦笑着说:“这感觉就像你知道火山要喷发,却因为站得太近被岩浆淹没了。”
散户最致命的误区,是把做空当成“看跌按钮”。实际上,真正的做空需要比做多更苛刻的条件:对财报细节的变态级拆解(比如发现某公司把促销费用计入资本支出)、对行业周期的冷血判断(比如预判芯片短缺周期反转)、甚至要对市场情绪有反人性的感知。有时候我觉得,做空者得像一个躲在暗处的侦探,既要有证据链思维,又要懂群体心理学。
—
三、当下A股:做空更像一场“戴着镣铐的舞蹈”
最近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,有人高呼“中国做空时代来了”。但以我这几年的观察,A股的做空生态更像是个半成品行为艺术——融券券源稀缺得像沙漠里的矿泉水,个股期权门槛高得吓人,更别提那些隐形的窗口指导。有时候你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完美标的,却发现自己站在一扇玻璃门前:看得见机会,但找不到钥匙。
这种环境下,做空反而成了一种诡异的信仰游戏。你得相信自己的研究足够穿透信息迷雾,相信监管不会突然“父爱主义”发作,甚至要相信对手盘不会用资金优势强行拉爆你。去年某地产债暴雷前,其实早有机构通过信用衍生品隐晦做空,但很少有人敢大声说出来——在中国市场,有时候“政治正确”比财务正确更致命。
—
尾声:做空者的孤独与救赎
现在我依然会小仓位做空,但早已不把它当作盈利手段,更像是一种保持清醒的仪式。每次按下卖出按钮时,总会想起《大空头》里那个被所有人嘲笑的Dr. Burry——他赌对了次贷危机,却赔上了半数客户和几乎全部人际关系。
或许做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赚多少钱,而在于它强迫你与狂欢保持距离。当满屏都是“万亿赛道”、“颠覆式创新”时,做空者是那个躲在角落冷冷提问的人:“如果这一切都是错的呢?” 这种质疑本身,就是对抗群体癫狂的最后防线。
老陈后来还是坚持做多,今年在光伏股上回了血。上周喝酒时他拍着我肩膀说:“你们这些做空的啊,就是活得太较真。” 我抿了口啤酒没接话。心里想的却是:如果没有人较真,瑞幸的咖啡渣现在可能还埋在财报里发霉呢。
(完)
原创文章,作者:林凤百科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mftsp.com/4319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