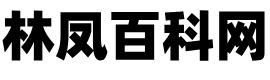去年深秋,我在河北某县城郊外见到一座废弃的光电产业园。生锈的龙门吊斜插在荒草中,办公楼玻璃碎了大半,宣传栏上”东旭集团战略合作项目”的字迹尚未完全褪色。当地出租车司机嘟囔着:”投了八个亿,热闹了两年,现在连野狗都不愿意进去避雨。”
这让我想起古希腊传说中的米达斯王——那位能将一切触摸之物变为黄金的君主。现代资本市场上,某些投资机构何尝不是在扮演米达斯角色?只是被点石成金的,往往是PPT上的估值模型和新闻通稿里的战略布局,而非实体车间里的生产线。
东旭系的资本运作堪称行为艺术。当你在财报上看到那些精密如瑞士钟表的产融协同模型时,很难不被这种工业与资本的诗意结合所打动。他们甚至给每个产业园都取了诸如”光电谷”、”新材料灯塔”这样充满未来感的名称——这命名美学堪比房地产商的”威尼斯水城”或”普罗旺斯庄园”,本质上都是给钢筋水泥注射致幻剂。
但真正令我后背发凉的,是资本炼金术背后的认知暴力。当某个县城主要领导陪着投资人视察规划沙盘时,当地方电视台反复播放项目签约仪式的特写镜头时,整个区域的集体理性仿佛被施了催眠术。我曾见过某开发区把三十年土地收益权质押给资管计划,换来东旭系旗下某个子基金的优先股——这种金融创新简直像是在用手术刀给活牛剥皮,还要夸赞切口整齐漂亮。

或许我们该重新理解”投资”这个动词。在传统认知里,它意味着播种、培育、等待丰收。但新派资本玩家把它变成了魔术表演:你看见他们往礼帽里放进去一只兔子,转眼就拎出来一头大象,观众还来不及鼓掌,整个戏台已经连人带道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留下的只有尚未付清的工匠工资和银行信贷员的失眠夜。
特别讽刺的是,这些项目的竣工纪念碑往往比厂房设备更耐用。我在三个不同省份见过几乎完全相同的汉白玉纪念碑,刻着豪迈的致辞和投资数据,风雨侵蚀下依然字迹清晰,而背后的厂房早已锈蚀得认不出本来面目。这些石头或许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谜题:为什么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企业,如此热衷于给流产的野心立传?
有私募朋友曾私下辩解:”我们本质上是在做压力测试,检验地方主政者对现代金融话语的耐受度。”这种论调让我想起19世纪欧洲的颅相学家,他们用游标卡尺测量殖民地原住民的头骨,来证明文明等级的差异。现在资本测量的是地方发展焦虑的刻度,以及制度弹性空间的极限。
当某地法院开始拍卖某产业园的剩余资产时,我在拍卖清单里看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标的物:12套仿红木老板桌、3尊铜铸招财蟾蜍、未拆封的智能会议系统——这些曾经支撑起资本神话的道具,如今像婚宴剩下的酒水般被折价处理。而真正值钱的土地使用权,早在三年前就通过复杂的分层设计证券化了。
或许我们该给这种投资模式发明新词:”幽灵投资”可能比较贴切。它确实能带来税收、就业和GDP的幽灵,这些幽灵会在统计报表里跳舞,在政绩简报里歌唱,唯独不会在深夜的厂房里点亮一盏真正的灯。
站在那片荒草丛生的产业园里,我突然理解为什么中世纪炼金术士要兼修神学——当点石成金的咒语失效时,总需要向更高阶的力量求助。而现在,当资本炼金术显形之后,我们该向谁祈祷?
原创文章,作者:林凤百科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mftsp.com/4005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