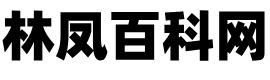在基金会搬砖,到底是镀金还是吃土?
上周和大学室友老陈喝酒,这哥们毕业后进了某教育基金会,一干就是五年。酒过三巡他突然问我:”你说咱们这代人,在基金会干活算不算正经事业?” 他无名指上的婚戒在酒吧灯光下忽明忽暗,像极了他此刻飘忽的眼神。
我认识的老陈曾经是个热血青年,大四时举着”用爱发电”的横幅在招聘会横冲直撞。如今他负责的留守儿童项目,要戴着安全帽在滇西山区爬三个小时土路,回来还得给捐方写充满诗意的感谢信。”上次那个互联网新贵来考察,指着破教室问为什么不用AR教学。”他苦笑着晃荡杯中的威士忌,”我总不能说这笔钱刚给孩子们买了过冬的棉鞋。”
基金会这地方有意思得很。你说它体制内吧,年终奖要看募款业绩;你说它商业化吧,同事里多得是放弃投行offer的理想主义者。去年他们部门来了个牛津回来的95后,第一天就建议用区块链做善款追溯,三个月后哭着辞职了——光是为了给山区老人发补助金,就得先手写两百份情况说明报送民政局备案。
但要说这是死水一潭也不尽然。我认识某环保基金会的项目官员,去年愣是把濒危物种保护做成了抖音爆款,现在带着当地村民搞生态旅游,捐款额翻倍不说,还真让几个盗猎分子转行当了导游。这种案例吧,就像雨天里突然劈进窗户的阳光,晃得人眼睛发疼却又舍不得挪开。
薪酬确实是痛点。做公益的朋友们聚会,结账时永远在AA制和”下次我请”之间循环播放。但有意思的是,他们手机相册里最多的不是自拍,而是某所希望小学竣工时歪歪扭扭的黑板报,或是被救助的流浪动物蹭脏的裤腿特写。这种精神股东的分红方式,华尔街的精英们怕是很难理解。
有次深夜加班打车,司机听说我在基金会工作,突然感慨:”我闺女去年差点辍学,就是你们这种人给救回来的。”那一刻堵在北三环的车流里,突然觉得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都变成了功德簿。当然这种感动持续不到第二天——上午就被审计报告里纰漏打得原形毕露。

所以回到老陈的问题,我觉得在基金会干活像在玩现实版俄罗斯方块。你要不断调整姿态接住天上掉下来的资源,又要时刻提防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压垮。但每当消除一行障碍时,那个”功德+”的提示音确实让人上瘾。
临走时老陈塞给我一包山区老乡给的苦荞茶,茶叶罐上还沾着泥土。”下周又要进山了,”他扯了扯勒脖子的领带,”虽然工资条看得心梗,但至少每天醒来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买单。”
霓虹灯下他的背影渐渐模糊成暖黄色的光斑,像极了他办公室里那盏总是接触不良的台灯。明灭不定,却始终亮着。
原创文章,作者:闲不住的铁娘子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mftsp.com/20390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