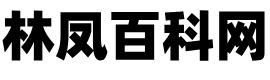芯片赌局与理想主义者的黄昏
三年前我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咖啡馆里,偶遇了一位头发凌乱的芯片工程师。他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上的电路图喃喃自语,手边放着一本被翻烂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。当我注意到他T恤上印着的“Make Chips Great Again”字样时,我们进行了一场改变我认知的谈话。
“大基金?”他听到我的提问时轻笑一声,搅拌咖啡的动作突然停顿,“你看这些资本就像追涨杀跌的股民——他们追逐的是财务回报率,而我们追求的是在硅晶圆上刻出0.1纳米精度的艺术。”
这个比喻让我怔住了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自2014年成立以来,媒体总喜欢用“国家队出征”、“芯片突围”这类宏大叙事,却很少提及那些在无尘车间里日夜倒班的工程师们。我记得那位工程师指着窗外华强北川流不息的人群说:“这里每天交易着千万个芯片,但有多少人知道Arm架构和RISC-V的区别?大基金投了上千亿,可真正的战场在人才争夺上。”
有趣的是,去年我参加某半导体峰会时,听到两位投资人争论是否要投某家光刻胶企业。穿定制西装的那位说:“这赛道天花板太明显,不符合我们的退出预期。”而另一位戴着智能手环的年轻人反驳:“但日本断供时,这家公司能救活三条产线。”你看,资本视角与技术视角的割裂如此真实——大基金既要算政治账,又要算经济账,这种双重人格注定了它的步履维艰。
我特别注意到二期基金投资方向的变化。相比初期狂扫晶圆厂,现在更侧重EDA工具和半导体设备。这种转变很像围棋高手从中盘厮杀转向布局基础——毕竟买再多的ASML光刻机,也不如培养出自己的蔡司镜头团队。但说实话,我最担心的是“创新者的窘境”:当所有资源都投向追赶现有技术时,谁来做下一代碳基芯片或量子隧穿器件?
有个现象很有意思:大基金投资的企业总喜欢在通稿里强调“国产替代率”,但我在供应链调研时发现,很多企业所谓的突破只是在进口芯片上打磨logo。这就像武侠小说里给宝剑镶宝石——外观唬人,实战时照样崩刃。真正的技术突破应该像中微公司的蚀刻机那样,能让台积电的工程师特意飞来上海学习。

最近某地被投企业爆雷时,我和几位行业老人喝酒。其中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做晶圆的老工程师醉后坦言:“现在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电子厂,这不是基金能解决的。我们那会儿在车间调试设备能三天不睡觉,现在呢?连拧螺丝都要找说明书。”这话虽然偏激,却戳中了产业投资最痛的软肋——资本可以买设备建厂房,但买不来工匠精神。
或许我们应该重新理解“国家基金”的定义。它不该是撒钱的天使投资人,而应该成为技术领域的“风险共担体”。就像二战时曼哈顿计划不是靠市场机制实现的,真正卡脖子的技术突破需要超越投资回报率的战略耐心。我听说某个院士团队在研发存算一体芯片时,连续七年拿不出商用成果,但大基金始终没有撤资——这种容错机制才是突围的关键。
站在2023年的节点回望,大基金最成功的可能不是催生了多少个独角兽,而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认知体系。现在连出租车司机都能和你聊两句芯片制裁的影响,这种全民级别的技术觉醒,或许比任何财务回报都珍贵。
离开华强北时,那位工程师送给我一枚晶圆钥匙扣:“记住,芯片的本质不是硅原子,而是人类试图用秩序征服混沌的野心。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——当千亿基金潮水退去时,最终留在沙滩上的应该是这样的理想主义闪光,而不只是审计报告上的数字。
原创文章,作者:闲不住的铁娘子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mftsp.com/19288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