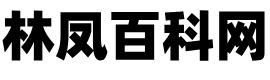当文化基金会不再只是“给钱”的机构:一个山西观察者的思考
去年深秋,我在平遥古城的一家老茶馆里偶遇了一位地方戏老艺人。他捧着已经掉漆的三弦,苦笑着说:“上面拨下来的钱倒是不少,可我这手艺,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”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——文化发展基金会的真正困境,或许从来都不在于资金的多少。
山西省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些年没少挨骂。有人说它“钱撒得漫无目的”,有人嘲讽它是“文化界的慈善施舍者”。但作为一个跟踪观察他们项目三年多的局外人,我倒觉得问题恰恰相反:他们太想做得“正确”了,以至于忘记了文化本身就该带着点“野性”。
我记得去年他们资助的一个项目——把太行山区的民间剪纸数字化。表面上看无可指摘:保护非遗、科技赋能、永久存档。可当我真正走进那些剪纸老人的作坊,听到的却是这样的抱怨:“他们让我们把祖传的花样都扫描进电脑,可我最想教城里娃娃的是怎么握剪刀啊!”
这让我想起人类学家项飙说的“附近的消失”。我们的文化基金会是否也在无意中制造着另一种“附近的消失”?当我们过度追求可量化的文化产出——建了多少非遗馆、录了多少小时的地方戏、出版了多少本文献——是否忽略了文化最本质的血肉,是那些藏在巷陌深处的、混乱而鲜活的生命力?
有意思的是,基金会内部不是没人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某个深夜,我和他们一位项目主管喝酒时,他吐露真言:“我们现在考核KPI要看’辐射人群数量’,你说,我该怎么证明一位老银匠花半年时间教一个徒弟,比办一场万人非遗展览更有价值?”这话带着三分醉意,却道出了七分现实困境。
或许我们需要重新理解“发展”这个词。在古汉语里,“发”是破土而出,“展”是舒张开来的姿态。文化发展不该是博物馆式的标本制作,而应该更像山西老陈醋的酿造——需要时间,需要沉默,需要容忍那些看起来“没用”的等待。

我特别欣赏他们去年做的一个“失败实验”:资助五个青年艺术家回到晋商老宅住三个月,不要求任何成果输出。最后有三人交白卷,但其中一个在项目报告里写:“我在祁县老宅梁木上发现了祖父辈的账本残页,突然理解了什么叫’文化的毛细血管’。”这种难以量化的顿悟,难道不比又多一份光鲜亮丽的文化白皮书更珍贵?
说到底,三晋大地的文化基因从来都不是温顺的。从荀子的“性恶论”到柳宗元的“吏为民役”,山西的思想传统里始终带着某种倔强的现实主义。今天的文化基金会或许该继承这种精神,少些锦上添花的晚会赞助,多些雪中送炭的长期主义——比如资助某个县城剧团连续十年排演新戏,哪怕他们永远上不了央视中秋晚会。
离开平遥前,我又去听了那位老艺人的弹唱。暗黄的灯光下,他突然即兴改了词,把基金会资助申报表里的官话编成了讽刺小调。满堂哄笑中,我忽然觉得:这份敢于解构权威的鲜活,或许才是三晋文化最该被“基金”滋养的根脉。
(后记:文章写完第二天,听说那位老艺人终于收到了基金会特别项目的聘书——不是让他申报非遗,而是请他去太原的高校教即兴创作课。你看,转变总是在发生,虽然慢,但值得等待。)
原创文章,作者:闲不住的铁娘子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mftsp.com/18369/